北大诗人与诗歌的传奇
浏览次数:6932 次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03日
作者:西渡谈起北大诗人,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北大中文系一直是诗人窝。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一个出现,而是一伙一伙涌现的。三十多年来,这个诗歌的链条从没断过。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臧棣和我合编过一本《北大诗选》,收1977级到1996级北大出身的诗人78家 ,其中中文系出身的诗人51家,是当然的主力。
这些诗人有的本科毕业后即离开母校,有的硕士、博士一直念到学位的尽头,更有少数幸运儿至今仍在中文系或在北大其他院系任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中文系求学的经历都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同时也是其或平淡或传奇人生一个不平凡的开篇。对他们中的多数人,种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埋下的,精神的成长也由此开始。
收获的季节也许美不胜收,但它的开篇却无限精彩。当我打开记忆的仓库,也意味着回到一个不朽传奇的开篇,重临1980年代风云际会的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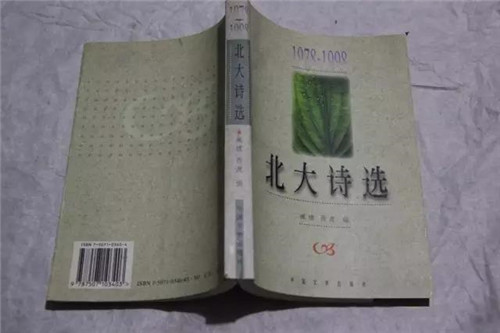
图丨《北大诗选》
1977、1978年两届同学多以小说名世,陈建功、刘震云、黄蓓佳、张曼菱等各领一时风骚。写诗的当然也有,1978级熊光炯就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但是说到中文系诗歌传统的源头,却还要归于1979级的骆一禾。
事实上,骆一禾也是新时期整个北大诗歌传统的确立者。不仅中文系后来的诗人都受益于他,中文系以外,海子、西川的写作在一个时期内也都受益于他。

图丨骆一禾
骆一禾是新的,同时也是旧的。骆一禾第一个勘破了中国当代诗歌“新”、“旧”的二分法。
他认为写诗是要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提供一个价值的基础和一种以行动为指归的诗歌精神。这样的文学抱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鲁迅以来还没有第二人。
中文系后来的诗人无疑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责任和雄心,从而使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诗歌事业时有一个深厚的基础和基本的高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这些诗人的写作中绵绵不绝、传承有序的人文关怀。
我和骆一禾只见过两次,都是在海子自杀以后。
第一次见他神情疲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伤。说话时却一例沉静安详,话语从他的唇间如滚珠溅玉一般流淌出来。一屋子的人都静静地听他说话。
第二次即是在海子朗诵会上。朗诵会开始前,骆一禾讲了话。还是那个沉静如溪水的声音,用了一种柔和的、低语似的调子,却直抵听众的心灵。那次骆一禾给臧棣留下的印象是“天才的演说家”。
骆一禾的发病很大程度上和海子之死有关。从海子逝世到他发病正好四十九天。在这四十多天时间里,骆一禾不仅和海子家人一起赴山海关处理了海子的后事,之后又作为海子的遗嘱执行人,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海子的长诗《土地》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并写了长序,另外还为海子的诗写了两篇高质量的批评文章,并多次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发表关于海子的演讲。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度的悲痛中进行的。
诗人邹静之记述了海子死后,骆一禾有一次参加诗人聚会的情形:“他不断地喝酒,几乎不吃饭菜,怕他醉时,已经劝不住了,夜里送他回甘家口的新家时,他说:‘我要这样,海子死后我太沉重了,我要把这些吐出去’。”他那篇后来广为传诵的《海子生涯》完成于5月13日,隔天他就倒下了。体现在这些事实里的伟大情谊使我相信,杰出的诗歌只能酝酿于伟大的人格。骆一禾是杰出的诗人,更是至情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海子是幸运的。

图丨1989年春海子去世以后,西川(左一)与骆一禾(左二)、老木、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1982级文学专业人才济济,拥有很多校园名人,写诗的不少,缪哲、邹玉鉴、张旭东、张华峰为其中翘楚。
张华峰时任五四文学社社长,邹玉鉴任诗歌组组长,缪哲则是诗歌组的副组长。
作为诗人,邹玉鉴当时在校园里名气最大,但真正具有成熟风格的诗人是缪哲。

图丨缪哲
缪哲有两个外号,一曰“大队长”,另一曰“恶和尚”。
“大队长”外号的来历不明,“恶和尚”的来源大约是因为他个子高,面黑发希,其声若钟。缪哲惜语如金,每开口,便觉一室之内嗡嗡有声。
缪哲的传奇之一是不讲卫生,据说他的被子大学四年从未洗过,而且绝少洗脚,只有在他的下铺魏同学提出抗议时,才偶尔一洗。
传奇之二便是“恶和尚”的“恶”了。同室张旭东吃饭喜欢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吃,美其名曰“最后总有一口香”,但他的这一口香却常常被缪哲一勺捞进自己的嘴里。他又常把下铺魏同学的夜宵吃掉,而且不管魏同学藏得多么严实,总能被他找到。魏同学找他理论:“你这人真是太不地道了!”缪哲自有话回他:“唉,我都承认了你还说我?你说我要是不告诉你呢?”如此夺人口中食,果然恶之甚矣。
缪哲的传奇之三是背《诗经》。据说,缪兄有两个月足不出户,静静地躺在他的脏被子里用功,竟把诗三百一篇不漏背完了。
缪哲写诗全出于不经意。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诗人趋之若鹜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其实他在当时已经是独具一格的诗人。
他的诗诙谐、睿智而富禅味。语言结合了文言的简练和口语的活泼利落,找截干净,绝无冗词赘语。
这样的诗在新时期中文系诗人中是孤例,在新诗史上似乎也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有老北大出身的卞之琳庶几近之。但是卞之琳的智慧诗做得吃力,缪哲的禅意却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可惜缪哲的精力后来用到别处,中断了他的诗歌生涯,致使中文系历史上少了一位可能的大诗人。
中文系的诗歌创作在1983级达到极盛,这一级的诗人也是后来一直坚持写作、留下硕果最多的。

图丨臧棣
臧棣在张华峰之后接任五四文学社社长。他长得高高大大,处处高人一头,生就一副开宗立派的气象。
他写于1984年《房屋与梅树》当时已是众口传诵的名篇。1990年代初,我对朋友介绍他时总是说:“大诗人。”如果说那时候还有人觉得我的话夸张,那么现在他在当代诗坛的大诗人地位早已确立无疑。
当然,当时北大诗人中对他的诗也有争议,一些人以为过于晦涩,书卷气重。贺照田曾说臧棣的诗以后将为无数学者提供饭碗。我自己从入校起就一直是他死心塌地的崇拜者。
臧棣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做事认真而守信的人,看重集体的诗歌事业甚于个人功利。
但是后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评点书评作者,却把臧棣列为信誉最差的作者。从一个最守时的绅士到信誉最差作者,我想在这一过程中一定包含了许多公开和隐蔽的错误。
尽管如此,这些错误只被严格限制于生活的领域,而在诗歌领域中,这个高大的诗人从来不犯错误。他对于诗歌的投入,在当代诗人中罕有其匹。
1990年代初,他就开始不断说忙。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快递公司,彼此要交换点东西都靠自己跑腿。为了省时,也为了省钱,他和我经常约在地铁口见面,他不出站,我也不进站,就站在站台台阶上说话。
有一次也是这样见面时,我问他:“你总说忙,到底忙什么呢?”他的回答令我惊异而感动:“写诗啊!”
他的创作数量惊人,胡续冬曾因之戏称他为“新诗的陆游”。我想他也许不是“新诗的陆游”,而是“新诗的杜甫”——在我看来,他必定要成为新诗的一代宗师。

图丨清平
清平有个玩物丧志的毛病,每有所好,必倾全心、尽全力。清平是资深的武侠迷,金庸、古龙、梁羽生无所不读,而最爱古龙。又有写武侠的雄心,不知做了多少精彩的开篇,害得很多朋友心痒难熬地等着,然后总是没有下文。上班后有一阵迷恋网游,竟把办公室当成了网吧。据说他最近又爱上了车,照他以前玩物丧志的榜样,也许中国又要多一狂热车迷。
清平上班后活脱脱把北大宿舍搬到了单位,昼夜不闭户。凡有人至人民文学出版社访友不遇,都在清平的宿舍歇脚。
宿舍中的家具除一张床上有一圈人形落灰较少外,余皆积灰数寸。又有种种别处绝难见到的古怪物什,如存放数年之年、坚若铁石的馒头、花卷,乌黑的枕头,数百双经年不洗的袜子。
这样的一个清平,结婚后成了举世无双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
不仅为太太写诗无数,又写歌巨量。某日值友人婚礼,清平清唱数阙,倾倒一片,把请来的专业歌手也听傻了。这是做丈夫的模范。
麦芒前几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中文系举办讲座一场,并约老友相聚。大家都欣然赴会,末了只有清平一个人爽约,问他原因,道:“女儿明日要考试。”听这话,人都要以为他的宝贝千金不是中考就是高考。实际上那时他女儿不过小学二三年级,所谓考试也不过平时测验而已。据说,每每女儿考试,清平便紧张失眠。其为女儿上心如此。这是做父亲的模范。
但我劝天下男子切勿让你的女友、太太结识清平,否则清平这名字就会成为你一辈子的紧箍咒。这可是我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

图丨麦芒
他比我高两届,却比我还小俩月。可见其人智力超群。据说麦芒平时读书不用功,而能每考必捷;象棋、扑克无所不精,扑克曾与同班孔氏庆东联手,打遍北大无对手。
如果说清平是1983级诗人中的道德君子,麦芒则属于1983级诗人中的浪子。
从本科起,麦芒就留了一头秀丽乌黑、令女生嫉妒的长发。他那一甩头的潇洒,不知倾倒了多少情窦初开或已开、北大或非北大的女生。他是北大校园里最无情的少女杀手。古龙有书曰“多情剑客无情剑”,他就是那“无情剑”。他杀人于无形的秘诀就在“无情”二字。多少青春少女、文学女青年想在他这里攻城略地,他按兵不动,一例杀之以无情。
麦芒本科时有言,本科生最聪明,博士生最愚蠢。他自己却一路硕士、博士地念下去,终于把本科生的聪明,换成了博士生的愚蠢。然后,长发一甩,携着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外籍女教师飘洋过海了。
麦芒的诗自有一种浪子的风华和潇洒,但在骨子里的是一种无言的深情。
他也是一个对诗体有深入研究和考虑的专家。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居留国外,他的诗在国内发表不多,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自己对他的诗也有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希望自己不久后可以有时间来进行这个工作。
戈麦、郁文、紫地、西塞和我于1985年秋天入学,住进32楼。从此到1986年夏,32楼达到了它1980年代人物鼎盛的巅峰状态。这一年,从1982级到1985级的才俊们齐集32楼三、四层,出出入入都是才华横溢的身影。那时传说在北大随便扔个馒头就能砸死一个诗人,形容这时32楼的情形,倒也恰如其分。
戈麦,本名褚福军。他开始在古典文献专业,主要兴趣却在经济学。
戈麦上中学时文理俱佳,高二分科时,受这位爱好文学的兄长的影响选择了文科。但在高考前夕忽生懊悔,并欲降级改学理工,以为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在这“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下,戈麦当时报的专业是经济,结果被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因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兴趣比较淡薄,后悔未上辽宁财经学院,甚至想弃学再考,在长兄的劝说下始到北大报到。
在北大,他同时上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并欲转经济系未果,因此很沮丧了一阵子。但他对文字发生兴趣却是很早的事。他四岁时即在长兄指导下开始认字,五岁时学二胡和绘画,八岁即与二姐、三姐一起登台演奏小提琴,在当地颇获称誉。上初中时已写过一些小诗。课余喜欢武侠、侦探小说,曾习武术、拳击。对体育的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和工作之后。
他看人眼光最准,有人因此说他“眼最毒”。毕业之际他对同学所作的预言大都为后来的事实所应验。有同学甚至说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与他两目相对,自己的庸俗便暴露无遗。
“戈麦”被用作他的笔名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戈麦每换一次笔名,诗艺上都上了一个台阶,而终于在“戈麦”这个笔名中找到了自己——某种坚实、严峻的东西。
1989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毕业生所住的38楼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航船,满载着绝望的哭号和抽泣。我并不是一个感伤的人,但在一片哭泣声中,也禁不住涕泪滂沱。而戈麦是唯一忍住没有哭的人。
在同学的纪念册上,戈麦留下了很多即兴发挥的警句。他给一位女同学的留言是:“做党的好女儿。”这位女同学很不高兴,大家却都佩服戈麦的勇气和看人之准。就是这位女同学,数年后在自己的婚礼上,面对上司和同事唱起了“党呵,我亲爱的母亲”,应验了戈麦的预见。
他在我的纪念册写的是:
是自由
没有免疫的自由
毒害了我们
志趣栏上写着:“狩猎、滑雪、爬山、赛车、阅读、胡说八道”。这些纪念册因为有戈麦的题咏才真正具有了纪念意义。
1985级以后,中文系依然不断有诗人涌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风云际会难免风流云散。就经历这些故事的每一个人而言,它开始也匆匆,结束也仓促。在这短暂的过程里,我有幸见证了智慧、才华、热情、友谊和胆识,也见证了牺牲、死亡、疯狂和悲怆。但是精神活着,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所记述的只是一个传奇的开篇。每一个从中文系,从32楼走出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是一颗漂流的种子,它将在随便哪一片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始新一轮的生长,延续古老而年轻的生命。精神也就在这过程中扩展了它的领地。
2010年6月8日
谨以此篇献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周年之庆

